摘要:廉政政策按照行为导向可以分为约束型与激励型两类,我国古代发达的监察制度使得约束型廉政政策成为腐败治理的主要手段。明初的重典治吏表明约束型廉政政策可以快速打击腐败,但超出必要限度的严刑峻法会产生反腐边际效应递减,需要导入激励型廉政政策矫正负外部性。以往激励型廉政政策多因陷入道德渊薮而效果不彰,雍正朝的耗羡养廉是技术范畴内的激励型廉政政策,通过裁汰陋规、禁止捐俸、限制耗羡用途等手段降低了治理成本,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实施激励型廉政政策是反腐败标本兼治、巩固治理成果的重要方向,耗羡养廉所展现的熟悉下情、不图虚功,因地制宜,灵活施策等优势,可以为当今一体推进“三不腐”提供可创造性转化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廉政政策;约束型;激励型;耗羡养廉;陋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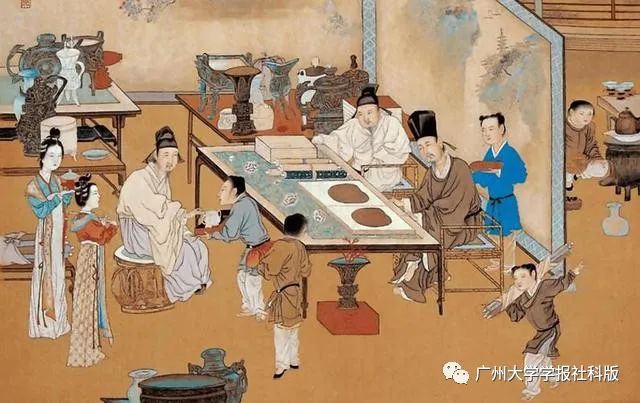
本文已刊发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或下方电子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此为网页推送版。
我国的廉政政策具有悠久历史,国家为了保证官员廉洁从政、打击腐败十分重视廉政政策的价值。廉政政策可以分为约束型与激励型两类,约束型廉政政策以“命令——服从”为特征,违反廉政政策的官员将承担严重的不利后果。激励型廉政政策以“行为——权益”为特征,遵守廉政政策的官员将享有一定的利益,包括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
由于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十分发达,统治者习惯于采用约束型廉政政策维护统治,激励型廉政政策只能依托行政、财政或风俗系统的,其独立性既难以被平民和官僚阶层察觉,其影响难以被统治者重视。学界对于古代廉政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显性制度,更多地以监察法制这一约束型廉政政策为视角,缺少对激励型廉政政策的深描。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史料的梳理,以雍正帝“耗羡养廉”改革为主要线索,指出技术范畴的激励型廉政政策能够降低腐败的预期损失和防控腐败的社会开支并且提高社会总福利,以期对当今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部署提供可资引鉴的经验。
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惩贪,其中的典型当属明太祖朱元璋。明代初期约束型廉政政策的覆盖范围、执行力度空前绝后,形成了历史上著名德“重典治吏”反腐体系。
(一)重典治吏的动因和表征
通过总结元代覆亡的教训,朱元璋认为“胡元以宽而失”,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推行重典治国方略,且朱元璋出身民间,深悉解官吏盘剥压榨底层百姓的不法作为,终生对官吏阶层保持不信任的态度。明初朝廷设立“拱卫司”监视官员,开厂卫制度先河;允许御史“风闻言事”,弹劾纠举;通过御制《大诰》赋予全国百姓捉拿任何不法官员上京受审的权利。
明初约束型廉政政策有三点主要特征,其一是惩治范围宽泛。明初惩治腐败既包括普通官员,也包括王公亲贵。据不完全统计,明初有十余万官员因贪腐处斩,诛戮过广导致官员严重缺额,不得不“戴死罪,徒流办事”,文人大多逃避出仕为官。其二是惩治标准严苛,《大明律》对腐败的惩治标准较前代严厉,如监守自盗四十贯,绞;枉法赃八十贯,绞。其三是惩治手段严酷。对于贪腐官员,既创设了法定耻辱刑,又有凌迟、族诛、刖足、断手、阐割等法外滥刑。
(二)约束型廉政政策的负外部性
过度推行约束型廉政政策挤占了激励型廉政政策可能存在的制度空间,官员清廉不仅难以俸养身,反而有可能因为激进的惩贪政策而被无辜株连。缺失物质激励也是约束型廉政政策难以落地的原因。由于明代官员实行低俸制,史学界有“明官俸最薄”之说。随着约束型廉政政策的演进,“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腐败依然难以彻底治理,朱元璋曾感叹“朕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他在晚年也曾反思一元化约束型廉政政策的局限,“设法防之,犯者日众。推恕行仁,或能感化。”根据社会学家贝克尔提出的标签理论,一旦国家或社会给人贴上罪犯的标签或加以羞辱,他们很可能一直是罪犯。霍姆斯据此主张,对于较轻的或初犯的腐败行为,不应过分渲染其不良效果,否则腐败就会借此滋长蔓延,呈现“越反越腐”的局面。
综上,严刑峻法一旦超出必要限度,所带来的反腐败的震慑效应递减;出于对官员的不信任而扩大化的监督纠举会滋生官僚群体的自我贬抑心理,致使惩贪效果不彰,亟需引入激励型廉政政策弥补制度失灵。
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认为,古代帝国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道德至高无上,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十分缺乏。技术问题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但又经常被道德掩盖。我国古代的激励型廉政政策也存在道德和技术两个范畴,道德范畴的激励可能因价值判断遮蔽甚至代替事实判断而呈现出片面性,甚至成为一种陷阱。
唐代名臣魏征认为廉吏难得,“夫吏之侵渔,得其所欲,虽重其禁,犹或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虽崇其赏,犹或不为。况于上赏其奸,下得其欲,求得廉洁,不亦难乎!”。仅依靠道德范畴的激励型廉政政策将难以摆脱“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
耗羡养廉是史上罕见的存在于技术范畴的激励型廉政政策,耗羡是指地方州县一级官府为弥补所征赋税银两在熔铸过程中的损耗、于正税之外附加的费用。该政策以钱粮数据、督抚奏销、层级配给等特征表现出高度精密性。
为何耗羡养廉始于雍正朝而不是更早?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无法突破道德范畴的障碍。康熙朝正项税收已经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但康熙帝沉溺于道德范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财政政策,不愿承受向民间加派税费的恶名。这种近乎于掩耳盗铃的做法导致地方州县私下加派耗羡达到“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私分耗羡已经演变为非正式的腐败制度,威胁到国家统治,有“天下之财,尽没于火耗”之说。
耗羡养廉政策可以被概括为:在现有税收基础上禁止加收火耗,将州县征收的火耗统一送到省布政司藩库,用于弥补无着亏空、官员增俸、政府杂项支出。笔者选取广东、山东、浙江三省作为样本实证考察耗羡养廉的实施效果。
(一)裁汰陋规,以上养下
明清时期京内外各级衙门和官僚吏役都存在陋规,除了平时向督抚赠送的节礼之外,又有堂礼、随礼、绸缎礼、契食礼等需要上交的礼品财物。陋规滋生制度性腐败,破坏了君主制下的中央集权,本级政府收入来源于下级,势必会影响其施政方向,在执行皇帝旨意时阳奉阴违,保护下属利益。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解火耗以养州县”。改革之后,下级没有必要也没有财力向上行贿,上级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监管下级。耗羡养廉的题中之义是裁汰陋规。广西布政使刘廷琛于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到任,上奏“奴才既遵奉圣训,一概革除,分毫不敢收受。”其他督抚也纷纷密奏皇帝,自耗羡养廉后,他们不再收取下属馈赠的陋规。
(二)禁止捐俸、限制用途
官俸是官员合法所得的俸禄,出自正项钱粮的地丁银。在耗羡养廉以前,地方财政一旦吃紧就要求官员捐出俸禄。皇帝禁止官员捐出俸禄,但仍有官员违反禁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违背常理的现象?大臣主动捐俸,表面是因公忘私的善举,背后却是帝制下“家天下”、财政体系公私不分的弊端。没有俸禄的官员为生计依然要向下索要,最终承受负担的还是民众。统治者既然受了臣工捐俸的“恩惠”,对于官员巧立名目地加派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雍正帝登基之处就下旨禁止捐俸,同时十分警惕耗羡养廉这一旨在适当优待官员以减少腐败的政策被异化。他给耗羡留出了极大的弹性,以防止公开征收耗羡后,耗羡具有了与正项地丁银类似的法律地位受到监管,官员又在耗羡之外向民间加派费用。此外,耗羡只能用于养廉和地方财政的小额赤字,禁止耗羡用于本应属于国家正规财政支出的事项。
(三)耗羡养廉的法经济学分析
技术激励型廉政政策在制定、执行以及变动成本均低于约束型廉政政策。就政策制定而言,约束型廉政政策以国家律令、判例的形式发布,其制定需要经过草拟、增删损益等多个步骤,需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方才颁布。耗羡养廉在短期能够确定政策的实施方案。就政策执行而言,约束型廉政政策的执行动员文官集团和普通民众的多数人,占用大量监督、执法、司法资源,耗羡养廉则没有增加原先征税成本,只是调整了一部分财政收入分配方式,执行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政策变动而言,约束型政策展现出较高的刚性而难以变动,耗羡养廉的实施中雍正帝授以各省较高自主权,允许其根据地方实际分配养廉银,因政策富有弹性而变动成本极低。
从社会福利方面来看,按照不同群体的对耗羡养廉的影响加以分析,发现改革增加了官员的合法收入,减轻了民众的负担。高级官员的收入名义上增加了,但实质上减少了。不过,高级官员的出身与经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耗羡养廉使其不必受陋规的污名困扰,以合法收入过上体面生活,可以追求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对于中低级官员而言,改革前该群体的总收入是普遍低于高级官员的,改革并没有过多侵犯其利益,而是通过取消法外收入、增加合法收入,并以约束型廉政政策的威慑力保障改革顺利实施。
(一)掌握下情,不图虚功
耗羡养廉能够从实际出发,决策者不贪图“民不加赋”的虚幻美名,将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给科层制中的各个个体。清朝面临着与胥吏共天下的治理危机,官员与胥吏有天渊之别,缺乏正向的职务激励、正常待遇和反向的职务惩戒制度导致吏员擅权和贪腐。雍正帝起初还陷于政治精英立场的傲慢,没有向胥吏、杂佐发放养廉银,随后认识到这一漏洞可能产生更大的腐败后,能够立即弥补。面对地方政府挪用养廉银,对廉政政策的价值有着清醒认识的雍正帝及时制止,因为即便是将养廉银用于合理的办公经费,仍会破坏激励型廉政政策最内核的养廉功能,产生新的腐败苗头。我国当今廉政政策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验,更不应脱离基层实际,求真务实历来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能力,应当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促进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识和把握,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推行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的廉政政策。
(二)激励为辅,双管齐下
激励型廉政政策与约束型廉政政策是反腐败体系的“一体两翼”。我国历代王朝善于通过“奖廉惩贪”来达到肃清积弊的效果。前文已论及过分倚重约束型廉政政策可能存在的负外部性和激励型廉政政策可能存在的道德陷阱,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不能良性互动,共同作为腐败治理的方式。对于技术范畴内的激励型廉政政策来说,更需要约束型廉政政策的保障。雍正朝的财政体系之所以能够负担各级官员的养廉银的同时还能减少百姓税收,就在于官员向国家让渡出了之前所得的大量非法利益,督抚一级官员或许有政治觉悟自愿让渡利益,广大中下层官僚让出利益却必须依靠约束型廉政政策的震慑作用。激励型廉政政策可以作为约束型廉政政策的有机补充,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共同用以治理腐败。
(三)因地制宜,弹性施策
耗羡养廉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改革,以山西为试点先行开展,一些大臣观望犹豫,雍正帝说“天下事惟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端耳。如以为可行,则可通行于天下,如以为不可行则亦不当试之于山西。”回应了改革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也打消了一些改革派督抚的顾虑。中国之治的特点在于全局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雍正帝推行改革注重因地制宜,妥善处理央地关系,明确耗羡收支问题是地方事务,中央户部仅加以备案,给予地方充分自主权以确保各地能够有养廉的物质基础。对于各省推行耗羡养廉的具体措施不做统一要求,例如,江南地区作为清朝主要的税源地,平民承担的正项税负已经很重,原先耗羡水平就较低,所谓重赋轻耗。浙江省改革后耗羡率仅有5%左右,陕西省改革后的耗羡率为20%,表面上两省差距较大,但浙江省由于税基较高,实收耗羡并不会低于陕西官员,改革后两省官员的合法收入差别不大。倘若搞成“一刀切”的养廉政策,官员收入差距太大势必会产生新的腐败,换言之,地方政策的伸缩性为全国政策的一致性提供了保障。当今我国的廉政政策也采取了试点先行的模式,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试点,借鉴耗羡养廉的经验,地方对于监察体制改革后的遇到问题可以在中央授权的前提下率先尝试,尤其激励型廉政政策可以体现更多的灵活性,不同地区通过挖掘本土元素,厚植地域特色,培育各具特色的地方廉政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