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
作为一个较为年轻的学科和领域,STS跨学科研究缘起自西方世界在20世纪后半叶对科学的反思和各类社会运动的兴起。STS可以被解释为“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或“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两个不同的研究传统,但都涉及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STS由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技术史研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SEPP(Science, engineering, and public policy)等不同领域整合而来。在国内,STS也曾有过一定程度的建制化发展,但如今主要归属于科学技术哲学门类下。
本专题选取了十篇STS领域的文献,希望尽力为大家展现STS领域的不同声音。第一篇选自库恩的轰动性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本书也通常被认为是STS诞生的关键原因之一。第二篇是默顿的著名论文“科学与规范结构”。这篇文章被视作默顿规范的纲领性文献。第三篇到第六篇代表SSK中的几种不同进路。第三篇是布鲁尔所提出的“强纲领”,这也是爱丁堡学派最著名的理论之一。第四篇来自巴斯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平齐,他与柯林斯以“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理论闻名。第五篇是夏平与谢弗的批判史学进路代表作《利维坦与空气泵》。第六篇来自拉图尔与伍尔加重要的实验室人类学研究。第七篇选取了赵万里早期对SSK的研究,他是国内较早关注STS领域的社会学学者之一。第八篇来自技术哲学家温纳,他以“技术物中内嵌有政治属性”为核心观点。第九篇的作者徐秋石曾师从平齐。这篇独特的文章为我们展现了STS中的声音研究领域。第十篇文章的作者库克拉从偏向知识论的角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进行了分析评论。
鸣谢
专题策划人:王景略

文献列表

从现代编史学的眼界来审视过去的研究纪录,科学史家可能会惊呼: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这就好像整个专业共同体突然被载运到另一个行星上去,在那儿他们过去所熟悉的物体显现在一种不同的光线中,并与他们不熟悉的物体结合在一起。当然,那种事并没有发生过,科学共同体并没有经历地理上的迁移;实验室外日常事务依旧进行。尽管如此,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仅就他们通过所见所为来认知世界而言,我们就可以说: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科学像任何其他具有社会协作性的活动一样,也受到多变的命运的支配。但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即认为科学在诸事物中即使不处于主导地位、但也有突出地位,那些受此熏陶的人难以接受这一观点,因为这显然意味着,科学难免会受到攻击、约束和压制。在前不久的著述中,凡勃伦可能注意到了,西方文化关于科学的信念是不受约束、毋庸置疑和至高无上的。对科学的反感过去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胆怯的学者才会去考虑一切意外,不管是多么久远的事。但现在这种反感已引起了科学家以及普通人的关注。反理智主义的局部蔓延有流行起来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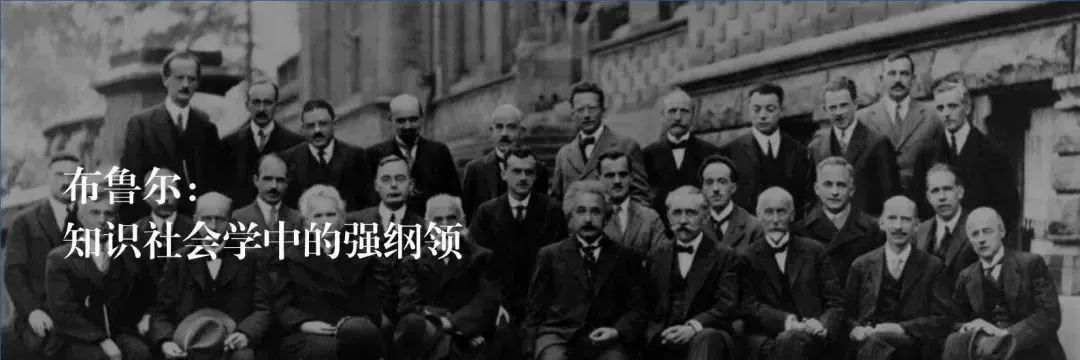
我首先将详细说明什么是我所说的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这样做可以为我以后考虑各种详细的反对意见提供所需要的框架。由于各种先天的论断从来都是镶嵌在各种作为其背景的假定和态度之中的,所以,为了进行考察,也有必要把这些背景性假定和态度突出出来。这将是我的第二个主要论题——只是在这里,与我们的科学观念有关的各种具有实质内容的社会学假设才开始出现。第三个主要论题将要涉及的,也许是知识社会学的所有障碍之中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也就是说,数学和逻辑学。我们将会看到,那些与我们所涉及的原理有关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技术性问题。我将表明怎样才能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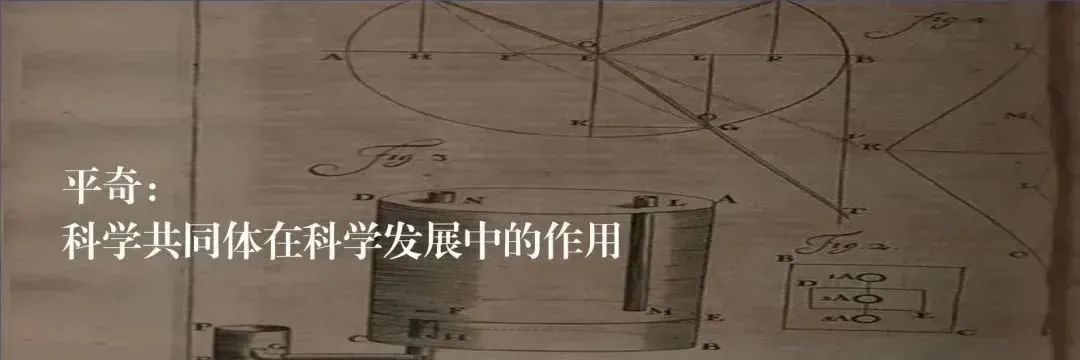
科学无疑是社会性的,但是,各种不同的科学社会学都沿用这一原则。可以根据社会学家在多大范围内将知识本身当作社会产品,把科学社会学分为弱日程和强日程。这篇文章叙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及主要领域、手段及争论的产生和影响。科学知识经社会构成的论点提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研究计划。而这一计划已经改变了科学的形象。

新社会秩序出现的同时,也摒弃了旧有的智识秩序。在二十世纪晚期,已确立的体制再度遭到严厉质疑。我们的科学知识、我们社会的构造、关于社会和知识之关系的传统陈述,都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当人们逐渐认清我们的认知形式有其约定俗成而人为的一面,就可以了解,我们认识的根本是我们自身,而不是实在。知识和国家一样,是人类行为的产物。霍布斯是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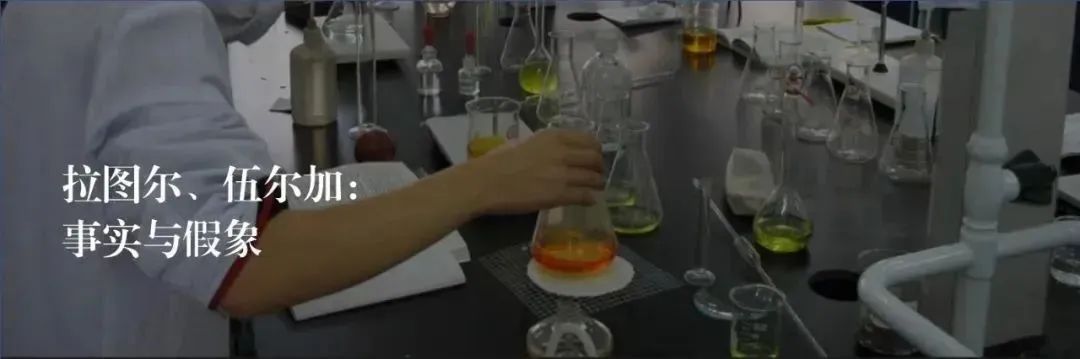
事实与假象并不分别对应真实陈述与虚假陈述。相反,陈述位于一个连续体当中,在每一点上对建构条件的依赖程度都有所不同,在某一点上,只有涵括了建构条件才能说服他人,一旦超出这一点,建构条件便无关紧要,或者成了破坏陈述“类事实”地位的企图。我们无意表明事实不真实或只是人为。我们不仅主张事实由社会建构,还想指出在建构过程中,科学家会使用某些装置藏匿起所有建构的痕迹。

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如果说在研究方法论上与自然科学有什么重要的区别的话,那便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极其小心地处理他们同被研究的对象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这种关系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研究工作展开得顺利与否,更重要的是它会对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产生反身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以科学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元科学实践,特别是科学社会研究,必须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表述与被表述之间建立一种共建(co-construction)意识、信任结构和合作意向。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正视技术物本身,也需考量其所处的环境脉络。如同柏拉图与恩格斯所强调的,航行的海船也许很需要一个船长及一群服从的水手。但停在船坞的海船就只需一个看管人。若要了解对我们而言何种技术与脉络是重要的及其理由,就得同时了解特定的技术系统及其历史,也需充分掌握政治理论的观念与争议。现代民众经常愿意大幅度改变自己的生活来迎合新技术,与此同时却不愿在政治面向做同样正当的大幅度改变。除非有其他更好的理由,对这些事务我们能建构比目前习惯性想法更清楚的观点,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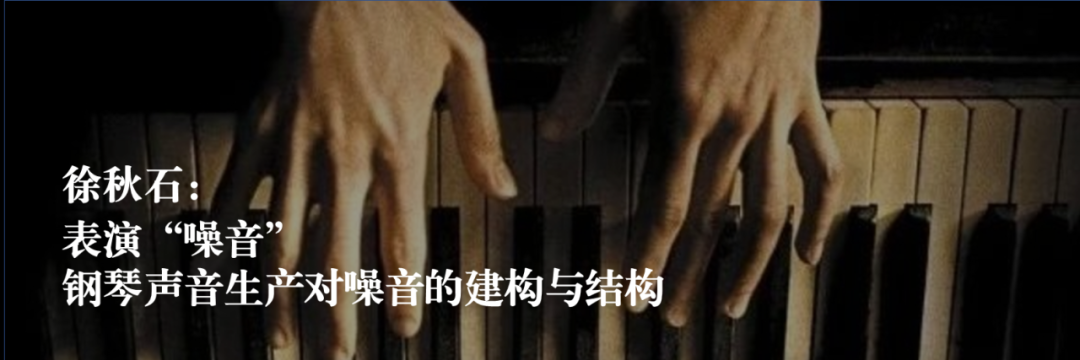
实际上,噪音处理技术的操作是一种艺术选择。在声音艺术的语境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噪音。然而,声音工程师的这一艺术处理往往是隐性的,多数钢琴家和声音工程师本人也对此并无意识。STS的噪音研究是新兴的跨学科领域声音研究(Sound Studies)的一个分支。本研究作为STS的声音研究的一个案例,展现了对被视为寻常声音现象的全新理解和阐释方案。
对一个具有无限范围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接受并不能推衍出对相对主义做出的承诺。根据接下来将揭示出的相对主义是不融贯的这一说法,这对科学知识社会学而言是一件幸运的事。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相对主义的立场并不能决定一个人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一个人既可以像布鲁尔和巴恩斯那样,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同时也可以是一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或者一个人可以是相对主义者,同时又否认社会原因引致一切事物。相对主义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两个不同的主题。更为明显的是,你可以是一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但同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建构主义者。所有你必须说的是,科学接受是社会原因造成的,但至少有一些科学假说或真或假,取决于独立的、先在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